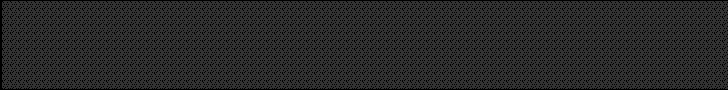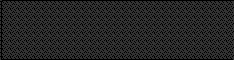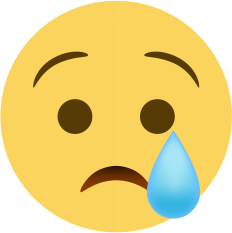第十三章 禮器
中國玉器中的禮器, 如: 六瑞、六器
第十三章 禮器
一 六瑞、六器
禮器,是三代時期國家用於封官拜爵、禮神、祭祀天地四方的器物,這有謂之「六瑞」和「六器」。
周禮春官大宗伯:「以玉作六瑞,以等邦國:王邦鎮圭,公執桓圭,侯執信圭,伯執躬圭,子執榖璧,男執蒲璧。」又記載:「以玉作六器,以禮天地四方:以蒼璧禮天,以黃琮禮地,以青圭禮東方,以赤璋禮南方,以白琥禮西方,以玄璜禮北方。皆有牲幣,各放其器之色。」
所有這引起禮器,以圭最為重要,圭為國家之重器。據周禮大宗伯的解釋:「不執圭者,未成國也。」可以知之。
周禮之書,所記載的玉圭,都是禮器的圭。圭形本源於石斧,是把原始崇拜石器的觀念,再與崇拜君權的觀念相結合,加以具體化地運用,用玉製作成為象徵政權的瑞器,並把圭規定了尺寸、用途,做為封官拜爵之用,作為天子諸侯的寶器,這便是朝廷禮器的圭。
六瑞、六器,以及天子祭祀山川薶沉之器、祈雨之器,這些玉制器物供朝廷使用,均見於周禮之書,都是周代開始使用的禮器。
歷代的注疏家,多依據周禮經文,臆度揣測,或繪成種種之圖形。如宋代聶崇義之三禮圖,把桓圭繪作 ,器中作兩豎直紋線。此種臆度作圖,雖不可信,但可反映出古人對周禮經文之見解。
禮記王制之記載:「王者之制爵祿,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,凡五等。」這是為「五等爵祿」的永載。周禮大宗伯的記載,雖不說五等爵祿,而列為「六瑞」,即加上天子也執一玉瑞,但也涉及五等爵祿。
「六器」之說,涉及五行方色,五行之說,見於書甘誓與洪範,兩書是春秋、戰國未所出之收。五行之說,大約是戰國時期的儒家,因循前人舊有的知識,加以整理而成。而「五等爵祿」,是戰國儒家依據西周舊有爵祿之名,而賦以等級之說。
周禮之書,考古學家有認為是戰國之作,是當時募集遺聞佚志而成,此說已為近人所共識,而這些大多出諸傳聞,不會是憑空所作。而周禮一書,雖曾經被劉歆點竄改,仍不失其價值。上述種種,明顯是戰國時經儒家加以理想化、系統化所修飾過的結果。迄今在先秦考古的出土中,仍未發現這麼多的品種和顏色。但商、周時期把某些類型的玉器作為等級標誌與朝祭儀中也是事實,也是有據可依的。
如「詩經」在現存三百零五篇中,包括「風」、「雅」、「頌」三部份,系周代王朝及北方各諸侯國史官、樂師經過長期收集、整理而成。「頌」是宗廟祭祀的詩篇,可信的程度相當高。而中國早在商周時期,即有史官的設置。「尚書·多士」說到:「惟殷先人,有典有冊」足見商代已有記言或記事的文獻。安陽殷墟出土的大批甲骨文,可說是商代後期的王室檔案,亦為目前所知的中國最早文字史料。
傳世史書以「尚書」為最早,收集了虞、夏、商、週四代統治者的號令訓誥,是研究三代的重要史料。
二 桓圭
禮記考工記玉人所記載之圭乃「杼上終葵首」,清吳大澂古玉圖考:「是杼上者,言其長而薄;終葵首者,言其廣而方也。」吳氏根據考工記玉人說到大圭時所說的「杼上終葵首」,考證出禮器之圭是平首圭。
圖 之圭是與圖 之圭都是桓圭。考據如下:
它們都是長而薄,廣而方;上端有一孔,孔兩面對鑽,相接處微有偏移,俗稱有「臺階」;圭身方正平直,下端最末處兩面微削成刃狀,是典型平首圭。合乎西周制禮的圭制。
陳大年認為:「圭本立體之器,其雙植乃指寺身兩邊之線緣,即全身方正平直。」
周禮大宗伯鄭注:「雙植謂之桓。桓,宮室之象,所以安其上也,桓圭蓋亦以桓為瑑飾。」賈氏疏:「檀弓雲,三家視桓楹,彼註四植謂之桓者,彼據柱之豎者而言。桓若豎之,則為四稜,故雲四植,植即稜也。此於圭上而言,下兩稜著圭不見,惟有上二稜,故以雙植言之也。」
此兩玉圭上端均有兩組(每組兩條)橫刻之極細平行直線,極可能就是古籍所指說之「雙植」謂之「桓」;橫刻陰線之下,有五組豎直平行陰線夾著的四條間隔,亦可能是古籍中認為分隔號四植,而謂之桓者。五組分隔號夾著的四條間隔,它與殷墟婦好墓中出土的一件玉圭(圖 )之間隔極為相似。
婦好墓中之玉圭,中刻五條深刻陰線,使圭面略呈四條寬的稍似微凸的間隔,近代專家稱之為凸稜,便認為是四稜,並引用「桓若豎之,則為四稜,故雲四植,植即稜也。」即與古說四植為「桓」的說法相合,於是稱它是「桓圭」了。這是近人的看法。但婦好墓出土之圭,是殷商之物,自非西周禮制之桓圭。如它是桓圭的話,則又可推斷商代時可能已有用圭作朝廷禮器,不過還沒有西周禮制之完備,以及有沒有什麼確定的制度也未可知矣。
此兩件玉圭乃真正的古器寶物,古籍中謂之雙植或四植,可能就是分別指此兩件圭的橫線、分隔號而言(而一組的兩條平行線,方能表示橫樑、豎柱之形)。三禮圖把桓圭繪作 ,中作二單分隔號,頂作屋頂之形,說明宋人認為桓圭與宮室上方有關,而作屋頂形,但非橫樑、豎柱之形。因其無實物可據,僅依據周禮經文,臆度揣測作圖,自不免有錯誤了。
禮記言圭,雖屢言「以素為貴」,但為分別等級,於素身之上,陰刻極細之數條平行直線,仍不為過,極有可能,當可為朝廷禮器制度所接受。而此兩玉圭之平行刻線極淺極幼,乍看之有如素面,與禮以素為貴者亦致吻合,故推斷應屬桓圭無疑,是為「公」所執之「桓圭」。
今此兩件桓圭實物的出現,大致可證信周代的五等爵祿及六瑞之說,其可信之程度將會大大提高,從而對考古界而言,將是一項突破性的重大發現,勢將有專注研究之必要,而極具史實的意義。
至於周禮考工記玉人所記圭的尺寸,可能就是戰國時代的尺寸。因周代經歷了漫長的八百多年,近九百年間,其尺寸定制也絕不可能一成不變。因為周公制定了禮、樂制度的時間是周初的開國時期,周公姬旦是周武王之弟,是協助武王滅商建周的開國大功臣,武王滅商後兩年病死,子成王年幼繼位,由周公代管國家政事,並制禮作樂。至東周時期,社會長期動盪不安,戰爭頻繁,到春秋末期禮崩樂壞,戰國時期各自為政,其制度已經完全崩潰了。度量衡制亦各國不盡相同,尺寸單在戰國時期亦已有異。
如西周尺之長度至今未明,所知者:存世商尺,合今尺一六.九五公分;上虞羅氏所藏的戰國尺是二一.七公分;秦漢時代的衛器制度規定的一尺,相當於二十三公分;玉莽在新朝建立的那一年(西元九年)曾下令統一全國的度量衡,根據銅丈實物測定,一丈是二三0.三公分。故考工記玉人所記的尺寸也只可能代表某個時期的尺寸而矣。
迄今為止,還從未在有出土紀錄中發現過一件,與考工記玉人所言的尺寸相符的朝廷命圭。因此,這兩件實物桓圭的面世,顯得特別有重大的歷史意義。
其尺寸考證如下:
圖 的圭,尺寸剛好是玉人所說桓圭的尺寸,桓圭九寸,合今尺二0. 公分,正好是此圭的尺寸。
禮記考工記玉人說:「命圭九寸,謂之桓圭,公守之;命圭七寸,謂之信圭,侯守之;命圭七寸,謂之躬圭,伯守之。」
因為秦為戰國七雄之最強國,玉人最可能採用最強國之尺寸標準。至秦一統天下,頒令全國統一度量衡制度,所規定的秦尺,確知相當於今尺二十三公分,亦應即戰國時代的秦國之尺寸標準,因秦統一天下後,正百事代舉,不可能立刻廢其原有之度量衡,而重改其制,以大增煩瑣。而史籍亦記載,秦統一之後,以秦國原有的制度為基礎,把法制和度量衡統一,故史籍此說是為可信。
圖 之圭正長二0. 公分,即戰國之秦國尺(二十三公分)的十分之九,即九寸,正合玉人所說的尺寸。故系戰國桓圭無疑。其平行陰線刻也較圖 之桓圭微深,反映出戰國時期禮器,可能 已不及西周初所訂禮制之那麼嚴謹。
反之,可證圖 之桓圭,長二 . 公分,因尺寸之不同,故推斷必屬西周初或中期之禮器,從而又可反映出西周之度量衡確與東周末期的不同,已有了些改變。而戰國期間各國之度量衡亦確實不盡相同,故古籍中才載有秦一統天下後,即頒令全國統一度量衡之說。
今這兩件桓圭實物的存世,強而有力地可證:
(一)禮記一書的時代,是戰國儒家募集當時遺聞佚志之作,不是憑空所作。解決了歷代史學家對該書時代的揣測及爭論,從而深具重大的歷史意義。
(二)是歷史上第一次有實物可證:周禮一書,所載之事,起碼部份是有真實性,所以又可推斷其它尺寸或其它部份,均為可信或可信之程度相當高。但其所載之尺寸應僅是戰國時期禮器之尺寸,而未能代表西周之尺寸。